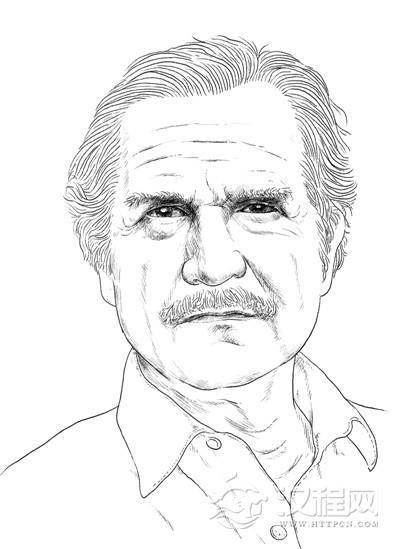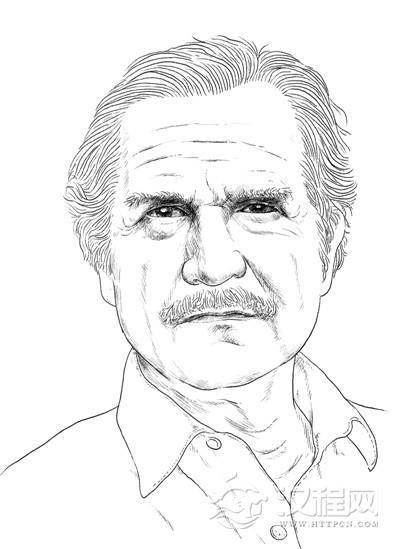
富恩特斯(1928.11-2012.5)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、墨西哥著名作家
5月15日,墨西哥国民作家卡洛斯·富恩特斯逝世,消息传出,不仅墨西哥举国哀恸,整个西语世界乃至全球读者都为之黯然。富恩特斯是拉美“文学爆炸”时期的代表作家,成就与马尔克斯、略萨和科塔萨尔比肩。他的作品深刻刻画了墨西哥的历史和现实,同时汇入二十世纪拉美文学浩瀚传统的一部分。本报特邀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译者、青年翻译家范晔撰文纪念这位故去的文学大师。
拉美文学的“引路人”2009年的某个夏日,我还在西班牙,随手打开电视,是作家弗朗西斯科·阿亚拉的访谈。换了个频道,还是。出门